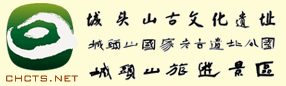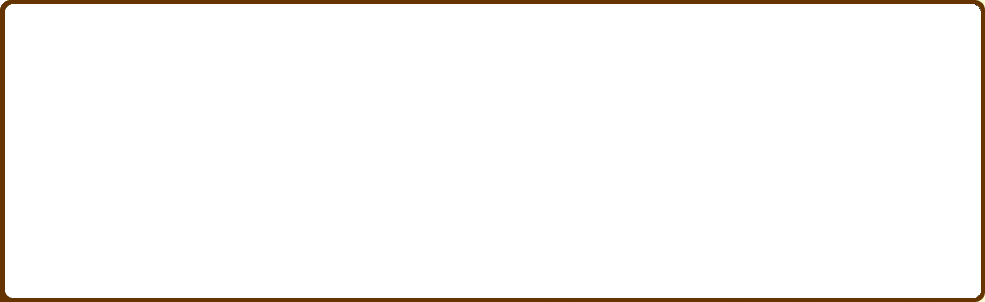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发掘记
洞庭湖区8000年的稻作材料和6500年前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解答人们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城出现在洞庭湖平原?”因为域的出现是聚落形态演变的结果,而聚落的出现和变化基础是食物生产的不断丰富。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剩余劳动,这样促使手工业逐渐成为专门的生产而独立出来,同时也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从事必要的管理工作成为可能。结果是在这些管理人员中引发出控制生产品再分配从而聚敛属于个人财产的欲望,导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解体。另一些方面,由于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变量的不平衡,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稳定食物来源的聚落产生了对富有聚落财富(首先是粮食)的觊觎,这样迫使富有聚落不得不兴建和逐渐完善防设。再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定居的普通性和稳定性,人们产生了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在原来维系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之外,又产生了浓厚的地域或领域观念。这些观念和行为的变化,直接的结果就是古城和古国的出现,就是由部落社会经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的递演变。
第三是发现和揭露了一座时代最早的完整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
宗教在古代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由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时期,酋邦的首领(以后演变为王)也就是宗教阶层的头,或者是虽然二者分属两人,但权力几乎相等。要在考古发掘中证明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踞于民众之上的酋邦首领或宗教阶层的头,主要靠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和大型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庙和坛。有幸在城头山,我们找到了大溪文化早期从事祭祀和宗教活动的大型祭坛。在同时期的各地发现中,它是最大、最完整也是揭露得最清楚的一处。1997年冬发掘东城时,即在正对着东门豁口角城内十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的建筑基址,在至高点有一个径近1米,深0.2米,底部平整、圆边极规则的坑=在坑中,平放着一块椭园形的大卵石。这个坑因太大太浅.不适合作为柱洞,理应另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另外,在黄土台的东缘发现数量甚多的大溪文化早期墓葬。在正东有三座墓,均为仰身直肢葬,有丰富的随葬品。678号墓还保存了完整的男性骨架,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在骨架左侧置放一小孩头骨。成人骨架颈部有非常精美的玉器,随葬磨光红陶器30余件,墓坑四角之外各有一座没有随葬品的屈肢葬墓。这座墓的墓主,一定具有不同寻常的身份。这个黄土台,我们当时就怀疑是祭坛。为了彻底弄清它的原貌,1998年冬我们对黄土台作了全面揭露,发现它略呈椭圆形,南北长径在20米左右,东西短径(因西部尚压在发掘区外)可能在12米左右,面积估计为250平方米,完全是在平地堆筑夯打而成,中间高,向边沿倾斜。在较高部位有五个与1997年冬发现的圆坑大小形状特征都完全相同的坑,其中三个由西北向东南成直线排列,距离均为4.5米。中间一个坑与不成直线的另两个坑则成等边三角形排列.这几个坑中也置放有大块卵石。在土台的最高部位,有一圈屈肢葬墓,其中一座墓的骨架葬于一大圆坑中,骨架下有黑色板灰,疑原有葬具.坑内随葬有牛的下颚骨和鹿牙,但没有陶、石器。我怀疑所葬为巫师。其它几座屈肢葬墓均一无所有,极可能为祭祀的人牲。在祭坑的东北、正东和东南、西部边沿,都叠压着大片的红烧土和厚达数十厘米的草木灰,或是祭祀建筑倒塌所致,或是祭祀活动的遗迹。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祭坛东北、东南、南部边缘之外(因西部、西北、西南部和北部边缘之外未能发掘)发现了数十个坑,有圆形的、方形的或长方形的,形状和坑壁均十分规整。不少坑内或有满坑倒扣的陶器,或有大型动物骨骼,如牛、犀牛的肩胛骨、腿骨,或是满坑的大块红烧土,满坑的草木灰,显然无法视作一般弃置垃圾的灰坑,在东北边沿外一个编号为315的坑内,上层倒扣着上十件陶器,均为釜、碗、碟一类炊具和食器,而其下,则是深近1米的草木灰,内有大量经过烧灼的炭化大米。联系到祭坛时代为大溪文化早期,而位置则紧贴着早先的水稻田,怀疑其作用除祭拜天地祖先外,最大的作用很可能是祈求丰收。
80年代初,当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喀左东山咀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距今5000年左右)和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发现后,当代中国考古的指导者苏秉琦教授高兴无比,评价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而今6000年左右的祭坛在城头山被较完整地揭露出来,无疑将为城头山古城所显示的洞庭湖平原初现的文明曙光增添无限的光彩。
八年来,我们在城头山发掘了近4000平方米,可算是已有了较大发掘的面积,但相对于这座仅城内即有8万平方米的城,仍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要彻底弄清城的布局,科学地评价它的发展水平及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尚需要继续作多年的发掘,作更多的揭露。相信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城头山这个宝地将有更多的古代文化的瑰宝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原载1999年第1期《湖南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