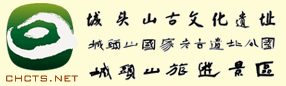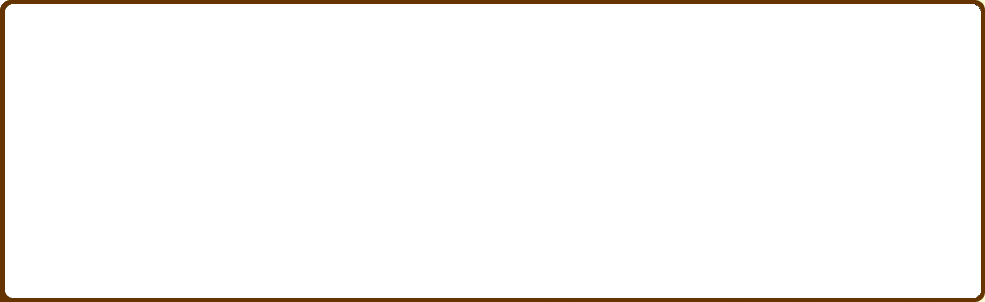废墟之上
一处废墟,一座圆形山包——城头山经年静静地躺在澧阳平原的巨大怀抱之中。
顽童在山包上戏耍,有伶俐小子摘一片柳叶含在口中吹奏,柳笛声声,三二只野狗追逐撒欢,四五头水牛悠然啃食……一些树木,一些杂草,一些坟茔,一些碎石瓦砾,山包环抱着一条断断续续的小河,附近错落着青瓦灰墙的农舍。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烟水人家。
因了水的泛滥,到处都是水雾柳烟。土里刨食被定格成悠远的画面,定格成永不褪色的乡村风景。没有人知道这个山包在平原深处躺了多久。有一天,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盯在这废墟之上。从此,人们走进了6000年前的华夏最古城址,走进了6500年前的最古稻田,走进了6000年前的最早最完整的大型祭坛!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精髓和灵魂终于得以昭天见日!
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早已闻名遐迩。城头山遗址的发掘,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至少提前了一千年。千年一叹的时间很漫长,漫长得每一种生命都不敢想象,而千年的时空却在城头山得以浓缩,浓缩成为人类的瑰宝。
一切曾那么熟悉,又那么平淡无奇,忽然发现每天踢踏的土地,原来藏匿着另一个世界!走在历史与现实的遐想中,风物与人文灵动交织,心灵与自然互为印证,蓦然醒悟家乡美得让人震颤。双手合十,庆幸没与废墟失之交臂;两目微阖,祈祷这自然与历史凝成的文明大放异彩。
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游人、专家、学者纷纷来此,触摸历史的肌体,倾听历史的诉说,寻求与先祖的沟通。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华文明亿万载,澧州古城七千年”,这是蒋纬国先生在台湾听到惊现城头山遗址后欣然题写的联语。
城头山不再是废墟,它是一座迷宫,一座圣殿,一座城市之魂。
断垣,废墟,陶片,残骸……不少人抱怨没看出名堂,我很释然。没有灵性的眼睛,哪怕在此走上千遭也会茫然。我们的先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一颗叫“家园”的种子,长久地被时间湮没,一直抵御着漫漫岁月的侵蚀摧残,终于在先祖后裔的心灵上长出感情的藤蔓,让民族远古的文明破土而出。
心即是景。其实,每一种源自生命的凝视,都会是一处美妙的景致。
寂寥的城墙让人进入一种绵亘数千年的宁静。那斑驳的城墙,一副沧桑的面孔。圆形古城雄伟壮丽,轮廓依稀可见。历经了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迁,部分城墙仍有四米多高。城墙是大溪文化早期、中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三次加高筑起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座6000年前的古城,当之无愧享受“中华第一古城”的殊荣。先祖们在城中间部位夯土抬高房基,成排的柱洞、柱础、门道、红烧土墙和墙基历历在目。当然,城内还出土了大量文物。形单影只的玉器、骨器、木器、竹器同时绽放出华光异彩,精美绝伦的各类陶器尝试着回忆往日的风光,大量支离破碎的陶片在陶场作坊周围哭诉往事。最大的陶器有五六十公分高,最小的陶器只比算盘珠子稍大。文物造型之异,工艺之巧,质地之优,纹饰之美,令人匪夷所思。这些无不显示城头山已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中心聚落,让人联想起曾经有过“烟火万家”的鼎盛,仿佛可以触摸到城市的气息——远古的、激起人悠远想象的味道。
一切都已远逝,没有鸡鸣,没有狗吠,听到的只是来访者杂沓的足音。瞬间,任何生命的谜底更显得扑朔迷离,缭绕出一片神奇甚至敬畏。
早于城墙一二千年的大溪文化前期的南墙,外面是巨大的壕沟,沟上架设了木桥,有木桩、木板、榫卯结构的木构件,有芦苇围着的桥头堡。附近出土了完整的桨、木艄,就像故事里的悬念,不断让人假以遐想:强健的艄公,踞乌篷船尾,唱着澧水号子,桡桨激流,横舟捕鱼。那时的澧水,该是怎样喧闹而又清澈的流过?置身废墟,一些绮思梦想总是扑面而来。
在壕沟的淤泥里,出土了稻谷、大米、豆类、瓜类、莲荷类等70多种植物籽实,还有象、鹿、牛、猪、鱼、螺等遗骸。在城头山东部又挖出了一块30多米长、4米多宽的稻田及配套灌溉设施。香港大学学者用日释光测试方法测算出稻田年龄为6500年!那些气息清新的泥土和籽粒饱满的果实,谁说又不是一个远古的图腾!如果把这里与2公里处的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联系起来,稻作农业已在城头山周边地区走过了二三千年历史。再把当今湖南著称于世的杂交水稻农业和城头山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其中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澧阳平原这块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一直在不断揭开它远古文明的面纱,发现了近400处史前文化遗址,而且时间顺序连贯距今3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种文化遗址的密集程度和时间连贯顺序,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城头山遗址就是这只摇篮中的一个孩子。轻轻穿越时空的隧道,就能看到城头山先民织就的一幅上山狩猎、下水渔捕、男耕女织的和平、安宁、幸福的美丽图景,就能听到乌篷船里回荡的袅袅渔歌,就能嗅到飘逸在古城头山上稻油的芬芳……
较早露出神秘面容的东门,一层压一层的大批墓葬及墓葬的陪葬品,昭示城头山那时已有明显的贫富等级区分,让人不能不思考阶级究竟缘起何时?在东门豁口即城内10多米处,有一个面积250平方米、用黄色纯净土平地夯筑的椭圆形垒址,周围祭祀活动的遗迹清晰可辨。那些满坑倒扣的陶器,满坑大量的动物骨骸,满坑大块的红烧土,满坑的草木灰及大量被烧灼的炭化大米,在这里均有分布。这是过去式,也是哀伤的前奏。很快,更有触目惊心的发现。那些或无头颅,或反绑双臂被杀殉者的人体骨架,令人毛骨悚然。阶级、统治、王权,甚至连国家机器也在这里初现端倪,让人轻易就找到某种归属。史家说,岁月越是平淡无奇,人民越是幸福恬然;历史越是惊天动地,人民越是水深火热。从这个意义上讲,筑城而居的城头山人,在历史的滚滚尘烟中,活得也许并不轻松。
失眠的废墟啊,你在凝满霜雪的日子里演绎了多少血腥杀戮的凄婉故事?袅袅哀号跌进废墟深处,听得清那是一种生命的倾轧和较量。六千年了,至今仍在澧水河上空缭绕,回荡……
伫立遗址之上,心境像秋日的天空一样澄澈。轻轻撩开城头山的面纱,上升的是文化,沉淀的是沧桑,张扬的是文明,沉睡的是历史。世易时移,那些象征暴力和权利的符号,又逐渐变成远古城市文明的构成元素